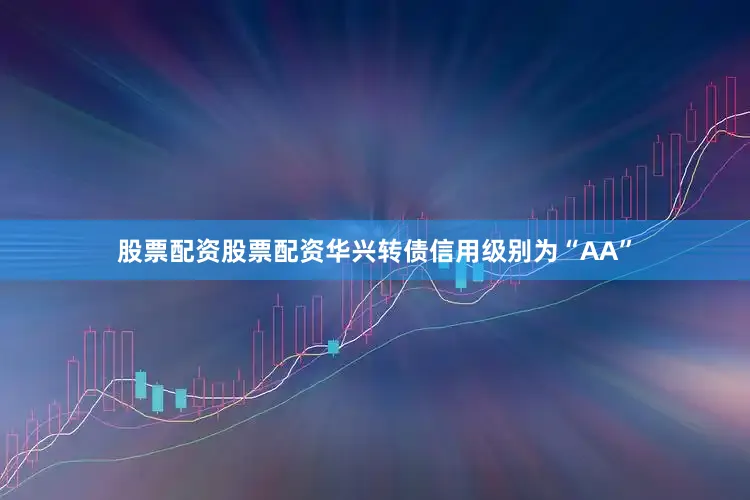战争终结的钟声敲响时,对60万被苏联俘虏的日军而言,地狱之门才刚刚开启。那些被军国主义“鼓舞”着走向战场的日本女兵在刺骨的西伯利亚寒风中颤抖着意识到:她们从战场幸存,却坠入了比死亡更漫长的炼狱。
西伯利亚冰原上的炼狱1945年8月8日,苏联对日宣战。很快关东军的太阳旗被另一面绘着镰刀锤头的旗帜取代,中国东北地区、朝鲜半岛北部、桦太与千岛地区的日本兵被苏联军队大量俘虏。具体的日俘人数不能确定,但学界基本认为在50万-60万人之间。
本来依照《波茨坦公告》,这些人在解除武装后应该被遣返回国。但同年8月23日,苏联国防委员会出台9898号决议,这些战俘被强制征用。而那些承担勤务、通信、医务工作的女兵们也在被征用之列。
一列又一列的闷罐车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冰原上穿梭,车厢铁皮上是一层又一层的寒霜,车厢内是挤挤挨挨的、面如死灰的战俘。踏上闷罐车时尚值夏秋之交,不少战俘身上仅穿着单衣,高纬度地区的极寒让他们无力承受。日夜交替之际,总有人发现新的“冻僵者”。熬过了这条死亡之路不意味着幸运,劳改营里的每一天都是炼狱。
展开剩余72%苏联也刚刚新生,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不好过,战俘营里的日子只会更为艰难。女战俘们不仅要承担和男战俘们一样的劳动量,还要面对更少的食物。被俘的日本女护士小野寺良子在日记里写道:每天配给的只有掺着木屑砂石的、拳头大的黑面包。
饥饿的阴影在战俘营中横行,连伙房倒出来的泔水也被她们视作“珍馐”。而除此以外,女战俘还会遭遇性剥削。夜幕降临后军官们的脚步就像催命符一样,被点中的女兵像货物般被拖往地下室。怀孕则意味着更悲惨的命运——简陋的强制堕胎或直接以“浪费粮食”罪名被处决。
比西伯利亚更冷的故乡严苛的劳动定额、恶劣的生存条件和医疗的匮乏成了一条高效的死亡流水线,战俘营里的死亡仅仅是纸面上的数字。有女战俘在回到日本后回忆,“收工路上,我们麻木地跨过冻僵的同伴尸体,泪水在脸上结成冰,却不敢哭出声。”
1946年开始,遣返开始了。按照苏联的计划,体弱者、工作先进者会被优先遣返。但许多女战俘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机会。而怀揣着希望踏上归途的女俘虏们发现,故乡的风比西伯利亚更冷。
踏上故土的那一刻,迎接她们的不是亲人的拥抱而是石灰粉——防疫人员向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全身泼洒消毒药水。骨瘦如柴的她们,皮肤被严重灼伤。而回到家庭的那一刻,更是成了不少女战俘终身的阴影——她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死在苏联,而不是回来让家族蒙羞。
有地方小报用侮辱性的语言报道她们的归国,右翼杂志《风评》更是堂而皇之将“娼妓”与归国女战俘关联。一篇《赤色慰安妇的归来》让多少女战俘不堪其辱,最终选择自杀。护士中村美知子在1995年东京证言会上的陈述更是令人难过, “检疫站官员当众呵斥‘张开腿检查布尔什维克细菌’,记者镜头直接对准我们裸露的身体……《读卖新闻》照片里我蜷缩着遮挡破衣的姿势,被杂志配上‘羞愧的赤娼’文字。”
女战俘们联合在一起向日本政府要求国家补偿,而日本政府则称她们是“不洁者”,不配得到补偿。在北海道网走市荒凉的墓园,217座无字碑排列成沉默的军阵。每块石碑只刻着六位数字——那是主人在西伯利亚的囚犯编号。正如思想史学者高桥哲哉所言:“她们在故乡遭遇的,是用道德匕首实施的精密屠杀。”
参考文献:[1]王蕾.在苏联日本战俘问题研究(1945-1956)[D].吉林大学:2013.
[2]赵玉明.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集中遣返过程的历史考察[J].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,2015(03):54-59+95-96. DOI:10.20018/j.cnki.reecas.2015.03.006.
发布于:云南省华夏配资网-配资网官网-股票杠杆-股票配资炒股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